起 点
张庆和/文
旭日喷薄而出,那是光明的起点;山间响泉叮咚,那是浩荡的起点;婴儿呱呱坠地,那是人生的起点;新年钟声悠扬,那是新生活的起点。
哦,起点!
你是刚刚啄破蛋壳的小鸟,蓊蓊郁郁的日子,正期待你的悦耳歌谣;你是刚刚绽蕾的花苞,芬芳馥郁的百花,不嫉妒你的娇艳妖娆;你是一粒萌芽的种子,无论长成参天大树,抑或生成茵茵小草,都将顽强地伸展一条条根须,不停地去探索大地的奥妙。
哦,起点!
你是零的突破,你是圆的创造;你是映亮心性的水晶,你是宣布诞生的公告。
回首来路,起点驱动了多少豪杰;展望天下,起点美丽了多少人生。起点不是虚无缥缈的云雾,起点不是遥不可及的彩虹。起点实实在在,起点可触可感:在每个人行走的双脚下,在迈出的每一寸步幅间,在每时每刻跳动的脉搏里,在起起伏伏深深浅浅的呼吸中。
在起点站立的,是人;在起点展翅的,是鹰。站立者,向往辽阔和求索;展翅者,仰望蓝天与翱翔。
起点不是落点,从起点出发,不论攀登高峰,还是走向远方,只要肯于行进,成功必定会一步步走来;起点不是终点,从起点出发,不论道路平坦,还是历经坎坷,只要坚忍不拔,身后总会是优美的曲线蜿蜒。
蜜蜂的起点是花朵:起点——落点——直至终点,循环往复的行程,把香甜散发,让芬芳缭绕;苍蝇的起点是垃圾:起点——落点——直至终点,肮脏的路径,把罪孽的毒菌四处传播。因而,起点才拒绝五花八门的诱惑,起点才鄙视假恶丑陋的角色。
哦,起点!
翻开崭新的日历,有如推开新年的大门:蓝天如洗,太阳鲜红;软风拂面,松柏泛青;弦歌悦耳,杂花繁盛。一条条大道在眼前铺展,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大道上,总是浩荡着向上、向前、永不停步的人生。
春 节
被春雨滋润着
被夏日照看着
被秋风吟诵着
被冬雪呵护着
一天接一天
很健壮很可爱的日子
节节生长
这最高的一截
叫做春节
春节如一块磁石
更像是一座站台
天上飞的
地上跑的
水上游的
南来的 北往的
拎兜的 背包的
揣着满怀喜悦的
扛着殷殷期待的
都一齐向它涌去
这站台很繁忙
这站台很热闹
鞭炮在吵
对联在笑
香气在飘
平安 欢聚
挤进千家万户落脚
浓浓的年味
随时随地都在引爆
作者简介:张庆和,原籍山东肥城,共和国同龄人,部队转业后定居北京。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作家协会会员,文学创作一级,第三届中国诗歌学会常务理事。系首届鲁迅文学奖初评组成员,中国作家协会多届会员资格咨询组成员。多年来一直从事业余文学创作,其诗文与儿童诗等在国内百余家报刊发表或转载。多篇作品入选中高考语文试卷和模拟试卷,以及“年选”、教辅、课外读物等不同版本图书300余种。出版诗集、散文集《好人总在心里》《漂泊的心灵》《哄哄自己》《灵笛》《娃娃成长歌谣》等20余部。
过 年
高巧林/文
春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带着千年习俗,透出万般风情,在人类文明多元色彩中永远呈现鲜明独特的文化个性,无法抹去,也不会被“洋节”同化。但是,时下越来越多的人在感叹——过年真烦、真累。这番感叹倒是回应了旧时所说的“年关”两字。现在大家生活丰裕了,没有了“年关”的窘迫,可为什么还要懒得过年、厌烦过年,甚至惧怕过年?我以为,原因是多方面的:肚子里经常裹着油糊糊的荤腥食料,过年时大吃大喝没胃口;身上衣着天天都是新簇簇的,过年时犯不着再翻啥新花样;人情味被物欲之流搅得酸溜溜的,过年时搞请客送礼太庸俗……
是的,要想好好过年也不容易。想来思去,还是借着过年的好气氛好心情,与家人亲友聚聚,看点文艺,读点书报,出门旅游观光,亲近初春里大自然,快乐又太潇洒。
我感谢老祖宗衍传下来的过年风俗。平时匆匆忙忙上班下班,只在嘴上唠叨“常回家看看”,而很少如过年时那样真心诚意去乡下尽尽孝心、叙叙亲情的;平时领了工资得了奖金,还会老是俗气兮兮盘计钱囊,而很少如过年时那样看得穿舍得消费,多买些东西,多享受点时尚;平时走在街上逛到商店里不时无奈于粗野俗之言行和脏乱差之环境,而很少如过年那样人人和颜悦色处处献美着喜,让人陶醉在暖融融的春天里······
作者简介:高巧林,中国作协会员,一级作家。当过老师和记者。曾任昆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昆山日报社总编辑等职。作品散见多种儿童文学报刊,入选多种儿童文学选本和中小学语文教科书、考试卷等。著有少儿长篇小说《送你一枝迎春花》《鸟窝村的孩子》《草屋里的琴声》《琴弦上的童年》《砖窑传人》《橹声回响》等多部。结集出版少儿中短篇小说集和少儿散文集10余部。曾获得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儿童文学》金近奖和“周庄杯”全国少儿短篇小说奖等奖项。多部作品被列入江苏省作协重点扶持文学创作项目。
三十夜间月光亮
龙良如/文
“你金竹冲五太婆今日走了。”
父亲告诉我这个消息时,我正在厨房准备午饭,刚才还明媚的心情,瞬间低落下去。
“她一向蛮健旺的。这次得了什么病?”
“我们不都才得过么?你五太婆是村里第一个因那病过世的人。”
千里之遥的家乡,此刻大雪初融,正是极冷的时节。我身处温暖如春的南国,内心亦冷到发颤。
五太婆是我见过的最慈祥的老人,见谁都眯眯笑,热情地招呼着,声音富有张力,带着极热烈的温情。
那年,奶奶把娘家侄女品姑姑介绍给五太婆的儿子,两家便成了亲戚,她对我们更热情了。新郎我原本叫爷爷,突然间却成了表姑父,一时不知如何称呼。我爷爷端着酒杯,朗声道:“只有世代的家族,没有世代的亲戚,之前怎么叫,还怎么叫。”
五太婆哈哈大笑:“对,对的!讲得好!”
小时候都喜欢走亲戚,既是家庭、又是亲戚的五太婆家,我们都极乐意去。无论是新年,还是平常日子,五太婆总会翻箱倒柜找出些吃货来,平分给大家。吃饭的时候,她不是端茶水,就是拿纸巾,生怕怠慢了来客。饭后闲坐时,她握着离她最近的那个人的手,关切地问长问短,灿烂的笑容,一刻也不曾离开那张满是皱纹、写满温暖的脸。
吃过午饭,我带女儿去午休,恍惚间回到家乡。我独自走在山道上,抬眼间,五太婆端坐在路边一块突起的石头上,笑眯眯地望着我。我记起她已离世的话来,自然惊了一跳。可是周边的路只此一条,又不好意思转头就走,只好硬着头皮停下脚步,怯声招呼道:“五太婆,您怎么在这儿?”
“走累了,在这儿歇一会儿脚。”还是那个熟悉的笑声,还是那张熟悉的笑脸。
犹豫了片刻,我轻声问道:“您老身体还好吧?”
“前些日子得了重感冒,发高烧,脑壳痛,喉咙痛,一身骨头痛,年纪大了,没得办法,搞了几日。现在没得事了,应该都好了,一点都不痛了。”五太婆边说边站起来,“听他们讲,这段时间得重感冒的人太多了,医生都看不过来,不晓得是怎么搞得咧?妹娃,你们都没事吧?”
我忍不住后退几步,笑着应道:“我早就好了,家里人也差不多都好了。”
“莫怕啊,妹娃,莫怕!太婆不会吓你的。”五太婆张着没有牙齿的嘴,乐呵呵地说,“你们都还年轻,要把身体搞好,好日子在后头。”
我不由臊红了脸:“好咧,太婆。”
“我明日打了一把铁夹,昨日却不见了。五嫂,你见到了么?”是故去多年的九太太,慢悠悠地从山上走下来,“日头快落岭了,你该回去呷早饭了吧?”
“你个老顽童,怎么地倒讲?”五太婆哈哈大笑道。
“嫂嫂您讲对了,我明明就放在灶上。”九太太背着手,一本正经地说。
两人都大笑起来,一晃眼功夫,她们都不见了。
“三十夜间月光亮,园里窃了茄子秧,聋子听见园门响,瞎子看见过了江,哑巴气得直骂娘,打发跛子出去赶,追到对门坳坳上,扯住辫子两巴掌,一看是个老和尚……”不知打哪儿传来悠扬的歌声,在山谷间久久回荡。
我打了个激灵,瞬间醒了过来。
午后的阳光,斜斜地穿透玻璃窗户,照在我们的床上,周身都热烘烘的,我侧头看了一眼女儿,她小脸红扑扑的,睡得正香甜。我翻身坐起,便坐在阳光下了,眼睛却睁不开了,抹了一把脸,满手湿漉漉的。
我没有拉上窗帘,想就这样坐着,呆在阳光下。
作者简介:龙良如,女,笔名良愚,侗族,湖南洞口人,现居深圳。洞口县作家协会会员、龙华区作家协会理事、深圳市作家协会会员。出版长篇小说《窑》。
(编辑:月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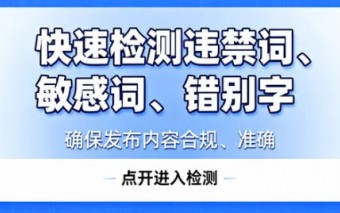




 体重轻就能半价旅游?提防“低价游”新套路
体重轻就能半价旅游?提防“低价游”新套路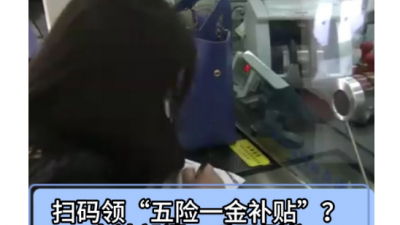 扫码领“五险一金补贴”?当心,是诈骗!
扫码领“五险一金补贴”?当心,是诈骗! 探秘 “银发专属健身房”:解锁老年健康社交新密码
探秘 “银发专属健身房”:解锁老年健康社交新密码 网络交友小心“甜蜜陷阱”
网络交友小心“甜蜜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