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养蜜蜂最早起于何时?说不清,爹也说不清,只记得阁楼上那堆残陈的蜂桶片有“道光”年号的毛笔淡迹。孩时,十几桶蜂堂而皇之地置在门面旁,屋檐下,前后窗台上,春暖花开,门前屋后,满天穿梭,芬芳四溢,小小的山村人家,沉醉在静谧的甜蜜中。
有日,爹对我说:“上山摆蜂桶。”他将空桶内侧喷了几口蜜,挂上扁担,掮上肩,噔噔地上路了。我像欢跳的溪水追其后。会稽山南端的山山岭岭,曲折迂回,陡峭挺拔,爹攀至崖下,刀劈般耸立的高崖底部里凹,杂草已铲,几块乱石上方座有石板,看出,爹早已瞄好风水。他将蜂桶放置在石板上,桶底锯有齿型的六、七个口对外。他背过身,瞄了瞄朝向:“蜂嗅觉灵敏,老远就闻到蜜香,成群的过往,就会进桶安家。”他割几把茅草盖在桶顶,压两片石,算是为它遮风挡雨。其实这地势,雨水不易打着,阳光倒有斜照,有两石压顶,显得稳重。“以后进山,常来瞧瞧,这里朝向好,会有。”
大约半个来月,进山砍柴,路过那座高崖,我架好柴担,攀爬而上,见有几只蜜蜂进出桶底的小口,心似灌蜜。傍晚,我和我爹一高一低上山,举桶瞧看,蜂仅拳头那么一小团。爹坐在不远处抽烟,云丝缕缕飘逸,我在附近采拮野花。待到天暗爹说:“采蜜的工蜂差不多飞回,包!阿端侬垫。”他端起蜂桶,我将青布围裙铺在石板上,拉平,他包扎好桶底,我们一前一后落山,将桶置在旧屋的窗台上。翌日清晨,它们与其它蜂桶的蜜蜂一样,忙碌开来。“阿农家又增添户口啦!”爹抽着竹管烟筒,在滋滋声中欣赏蜜蜂飞进飞出。
成功与失败,总是相随相伴。有次爹进山砍毛竹,见置在毛竹山上的那只桶口蜂踊如潮,纷飞繁忙。这里山高路险,人们极少上来,待知晓,已是大半桶蜂巢了。他试着拎拎,沉沉的,大部蜂房贯满了蜜。毛竹背下山,后半日回头,等天色昏暗,再用青布围裙包扎好往下背。那夜明月深匿,山溪竹涧沉浸在墨黑中。山路的每个湾头拐角,路旁的每棵松枫竹篁,甚至哪一段走几步,哪段溪跨几脚,在黑夜中我爹也有数,当然,也不在乎野猪出没,草蛇拦路,怪兽嚎啸,但意想不到的是过一泉流时,爹脚底滑苔,蜂桶“嘭”的坐在石头上,“轰”的一阵,蜂桶里的蜂巢砸在包扎的围裙上,万千辛劳的甜美顷刻坠碎,家破蜂亡,存活者疯癫般在桶里挣扎飞旋。爹此时苦不堪言,只得背起,浓郁的甜蜜透过青布包裙漫撒一路。我奶奶、我娘等到深夜还没见村头响动,担心出事,吩咐我们儿孙举火把进山接应。翌日蒙蒙亮,剩活蜂群倾巢逃往山野。
蜜蜂春夏最为忙碌。稻穗扬花灿烂时,蜂已繁殖成大家庭。“搬梯上去看看,每桶留一、二个皇房,多余摘掉。”爹说。山里人称之“摘皇”。蜂是母系氏族,每桶蜂只有一只母蜂,即蜂皇,比工蜂长且大,像马蜂。蜂巢将满时,整齐排列的蜂房中间二、三片的下端有几个小核桃大小的蜂皇房,蜡黄的房内躺卧蜂皇蛹,待她长大,就要另立门户,带领部分工蜂远走高飞。蜂皇越多,分家的工蜂越少,工蜂采蜜量少,过冬就难。这像家庭,缺劳力,势必生活艰辛。我家九口,爹娘农田劳作,空闲破竹编箩,奶奶年迈八十还用那已消磨成月牙型的篾刀划篾,孩子放学,首要的是完成家长布置的编箩筐数,然后做作业,戏耍。养蜂,对于家庭,是忙碌中的消遣,紧张中的松快。接蜂、割蜜是我爹的活计,其它由我们帮手。我爬上木梯,小心摘除皇房,每桶留最大的一、二个。每到此刻,我总要轻轻地抚摸这些密密麻麻的小性灵,对它们说上一阵悄悄话。
有一日,我砍柴归来,斗笠上插着数枝喷香的山兰,见屋檐下一桶蜂前成群结队翻飞,好似古书中描述的千军万马在调遣,“爹,分蜂啦!”我爹冲出门槛,头一仰:“快,泼水!”这话像条指令,全家老少,有的提桶,有的端盆,用瓢向上泼洒,成群的蜜蜂在六、七米的空中盘旋,仿佛是在等候蜂皇的命令。我们抓住时机,疯狂地将清水在空中洒成网,洒成片,在鲜红太阳照耀下,闪出七彩的光泽。最小的弟妹端着小竹碗助战,泼不到一、二米,成了落水人。空中的蜂湿漉漉,地上的人湿乎乎。蜂飞不动,被迫停在附近的树上结成团,黧黑的枝杆上突然间挂上一个褐色的包。
我爹来不及换衣,回头拎只空桶,喷上蜜,上树,他两腿夹着树杆,壁虎般伏在上面,将空桶支在蜂团上,一手扶桶,一手轻轻地撸蜂。那团蜂在他轻轻的抚撸中往上爬行。我们觉得他很费劲,但这活只能单干。待蜂入桶,他拎着蜂桶一寸寸退下,我们真为他担心。
一个新的蜜蜂家庭诞生了。
倘若发现不及时,倘若水泼不到领路蜂,它们就可能直奔山岭,山里有我家的几处蜂桶,可在会稽山的岗岗岭岭中,有多少家的蜂桶期待着啊!
蜜蜂不时增添,最盛时我家有24桶。
夏末秋初,蜂桶内上半部的蜂房封满了蜜。割蜜时节到了,孩童早早闻得浓醇的香甜,追问长辈早日切割。夜幕徐合,爹在长板凳上绑牢倒立的方凳,把一桶满腾腾的蜂桶斜倒其上,上方再斜扣一只喷有蜜的空桶。他端坐板凳一头,细心揭开倒斜蜂桶的木盖,嘘嘘地向里吹艾烟,蜜蜂感觉到了洪水般的烟雾,惶恐地向上遁逃。随着烟的升飞,它们阵阵密密地爬上空桶。木盖部蜂房的蜜在松明的光照下闪烁着晶亮。爹喜形于色,捋起衣袖,操刀挖了一块,填到早候身边的我的嘴里,又挖一块填给我弟,在五、六个小孩的啧啧声中爹挥舞钢刀,蜂蜜随蜂房哗哗坠入大罐。
男孩大多馋,好奇,不离蜂桶,谁料,散飞的一只蜜蜂不知何时进入我的开挡裤,顿觉痛苦时方知被蜇。我叔给我捏草药汁涂抹,边抹边调侃,一圈男女孩像看戏法,弄得我涨红小脸哭笑难言。这一夜,小东西红肿透亮形如光洁的玉烟嘴。小肚鼓涨,总尿不出。我爹上后山采回一种草药,捣烂敷上,稍刻,裆下水流潺潺,好不畅快。第二天,我仍蹭到爹身旁,再次期待切割的醇香。
每年割下滤过的浓稠蜂蜜,大多分送邻居、亲朋好友,分享几份甜蜜,换得满堂赞声。山里人重情谊,秋日谁吃玉米饼,春上谁咬麦馍馍,端上一小碗蘸就着,别有风味。山村人家,手艺活赶集赴市换现钱,食用的蔬菜、蜜类一般不出山。有时,给路经家门的歇客端上一碗蜂蜜水,那感激的笑靥,至今仍深深印在脑子里。
入冬,山花凋零,蜜蜂进出也少了。我们给蜂桶外扎稻草御寒。进九后,小瓷盘上排松针枝,洒蜜,置于桶底,让它们汲取营养,度过严酷的冬日,编织来年春天的童话。
(编辑:李月)







 体重轻就能半价旅游?提防“低价游”新套路
体重轻就能半价旅游?提防“低价游”新套路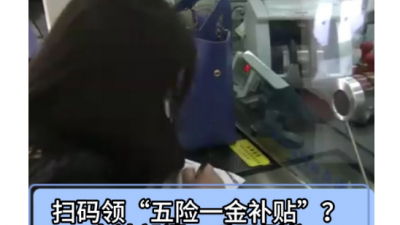 扫码领“五险一金补贴”?当心,是诈骗!
扫码领“五险一金补贴”?当心,是诈骗! 探秘 “银发专属健身房”:解锁老年健康社交新密码
探秘 “银发专属健身房”:解锁老年健康社交新密码 网络交友小心“甜蜜陷阱”
网络交友小心“甜蜜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