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娱乐作用,很大部分是通过文字游戏表现出来的。同世界上的其他文字相比,汉字在这方面具有独一无二的优势,因为它的方块结构最适合文字游戏。溯其源头,我们的祖先在创造文字时就已经种下了“游戏”的基因,比如“父”字,《说文》说它是“又(手)举杖”,而“母”字则是“象乳形”。另外,后人对文字的别解,也富含游戏成分,比如“天字出头即丈夫”“色字头上一把刀”之类,都是用字形来说明某个道理。汉代出现的谶纬之学,其中有些例子也利用了汉字可分拆的特性。比如《三国志》裴松之注中所引的童谣:“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犹不生”,便是用“拆字法”来咒骂董卓的。“千里草”为“董”字,“十日卜”为“卓”字。这种拆字方法在后来的游戏中甚为多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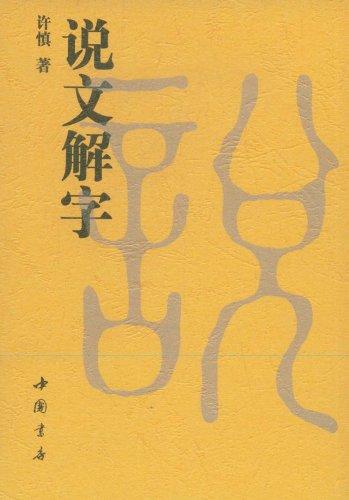
古代的文字游戏种类极其繁复,每一个种类都是一门大学问。比如灯谜,它的谜格就有近百种之多。再比如酒令,也绝不是在酒席上吆喝几声“三元及第”“四季发财”那么简单。单就以字行令而言,就有析字、拆字、合字、限字、偏旁、谐音等等,可谓花样百出,有着数不清的佳话。仅举“析字”一例,明代冯梦龙《古今谭概》记载韩雍和夏埙喝酒行令,商定一个字里要有大人、小人,并用两句谚语作结。韩雍先说:“傘字有五人,下列众小人,上侍一大人。有福之人人服侍,无福之人服侍人。”夏埙接着说:“爽字有五人,旁列众小人,中藏一大人。人前莫说人长短,始信人中更有人。”

文字游戏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可以从中学习文化、继承传统、丰富生活。当然,要继承好这份遗产,是需要花一番去芜存菁、删繁就简的功夫的。在这个问题上,“中国诗词大会”对飞花令的改造做得特别好。飞花令原是酒令的一种,规则很严格,难度非常大,比如所对的诗句格律要相对,所含关键字的位置也要有序移动。改造后的飞花令要求则简单得多,只要说出含有约定关键字且诗句不与双方说过的重复即可,对关键字的位置也没有要求。这样的改造合情合理,使得这一古老的文字游戏得以重生。

藏头诗作为一种文字游戏,原来也是种类繁多,其中最简单的一种就是把每句的第一个字连起来成为一句有意义的话。我在上海世博会期间写过这样一首诗:
上下奔腾万巷空,海天一色满江红。
人逢盛会票难觅,民入小康诗易工。
欢悦心情传叟妪,迎宾礼节教童蒙。
世间更有真诚在,博采千家得大同。
每句第一个字连起来便是“上海人民欢迎世博”。这也说明,传统的文字游戏是可以传递正能量的。
中国人最有资格也最有能力继承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比如有一种“叠句诗”,苏轼写过不少,其中有一首:“赏花归去马如飞酒力微醒时已暮”,应该这样读:“赏花归去马如飞,去马如飞酒力微。酒力微醒时已暮,醒时已暮赏花归。”这种写法看似很难,其实不难。我也曾经试写过一首,题为《为某读书会周年而作》:“以诗交友竞风骚浪里蛟龙吟浪里”,按上面的读法便是一首七绝。

现在写对联的人很多,但很有必要普及对联的基本常识。前些日子在朋友圈里看到一副上联:“鸟在笼中,恨关羽不能张飞”,是向大家征求下联的。我说且慢,这副上联不合规矩,是“病联”。因为它违反了对联最基本的规矩,那就是上联末字必须是仄声,而张飞的“飞”却是平声。面对不少朋友的疑惑,我打趣说,看在老朋友份上,我来给它治一治吧:联中因关羽、张飞而造成一种机巧,两人都是三国名将,姓名又恰恰都与鸟有关,鸟翅的一张一关,又与鸟笼的场景契合,所以这副上联出得不错。但“飞”字是必须改的,幸好关羽的“羽”是仄声,此联还是有救。可以先把两人颠倒位置,变成“恨张飞不能关羽”。这样一来,意思又不通了,还得改,可以把“不能”改成“只能”。鸟在笼中,翅膀扑腾几下,飞不出去,只能“关羽”。如此一改,意思更有趣了。

接下来便是对对子,要对好这样的上联还是有些许难度的。也巧,我忽然想起三国中的另外两个人:颜良和文丑。这两位袁绍帐下的大将,姓名也存在有趣的关联,所谓“绣花枕头一包草”。所以我对出的下联是:“人看镜里,笑文丑却是颜良”。这副对联,应该算是通得过的。“鸟在笼中”与“人看镜里”,结构完全一致,平仄完全相对,“仄仄平平”对“平平仄仄”。后面两个分句结构上没问题,但平仄上有一点小瑕疵。“恨张飞只能关羽”尽管是七个字,但不能把它看作七字句,因为它是“上一下六”的节奏,那么平仄的重点就是“飞”“能”“羽”三字,在这里,“飞”字最好用仄声,构成仄平仄,但从意思上看已经无法改动了。好在这不算是大毛病。下句相应的重点是“丑”“是”“良”三字,构成仄仄平,与上句的平平仄,也算对起来了。
之所以详言此事,是想告诉朋友们,文字游戏就是这么有趣,它是完全可以古为今用的。
(编辑:映雪)







 体重轻就能半价旅游?提防“低价游”新套路
体重轻就能半价旅游?提防“低价游”新套路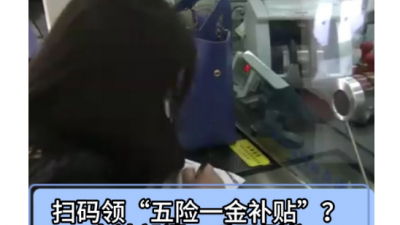 扫码领“五险一金补贴”?当心,是诈骗!
扫码领“五险一金补贴”?当心,是诈骗! 探秘 “银发专属健身房”:解锁老年健康社交新密码
探秘 “银发专属健身房”:解锁老年健康社交新密码 网络交友小心“甜蜜陷阱”
网络交友小心“甜蜜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