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去会尴尬的店、凑齐游戏的人数、去赏樱的地方占位子,在只需要凑一个人的情况下,请使用这项服务。”森本祥司号称“什么都不做的出租先生”,却由此获得关注。
2018年6月,森本祥司开始在推特上出租“什么也不做的自己”,让无所事事有了合理名义和用武之地。
活了35年,森本祥司发现自己最擅长的还是“什么也不做”。显然,这个时间还不算太晚。
大阪大学研究生毕业后,他在出版社做过编辑,也尝试过自由职业,但每份工作都坚持不了多久。
和很多厌倦上班的人一样,他坦承自己不大适合工作,也难以适应“日复一日见同一群人、做同一件事”的职场身份,于是自然地转向了“也许自己适合什么都不做”的想法——但这个看似轻率的结论,并未走向一个消沉的结局。
尤其是在SNS上发现以“职业被请客”为生的博主中岛太一之后,森本反问自己:人不工作、不赚钱是活不下去的,但如果不拘泥于社会常识,什么都不做,能照样活下去吗?

在东京工作5年、即将离职回老家的女孩,希望森本陪她度过在东京的最后一天。/《什么都不做的出租先生》
一方面怀着实验的心态,一方面顺应自己不想工作的心意,2018年6月,他开始在推特上出租“什么也不做的自己”,让无所事事有了合理名义和用武之地。
如今,森本在推特上有26万粉丝,他的业务公告这样写道:“您只需支付1万日元、国分寺站的交通费以及可能产生的各种餐饮杂费即可。但除了喝酒和简单的应答,我什么都不做。”
接受NHK《纪实72小时》节目组采访后,森本和他的出租业务瞬间成为社会话题,并在两年内书籍化、漫画化。今年春天,东京电视台根据他的事迹改编的短剧《什么都不做的出租先生》也随之播出。
陪同做痔疮手术、旁听法庭审判、等待公布医生资格考试结果、凑齐打牌的人数、帮忙到赏樱的地方占位子……在只需凑一个人的情况下,都可以使用森本的这项服务。

见过森本后,这位大叔受到启发,想做“什么都做的出租先生”。/《什么都不做的出租先生》

迄今为止,森本收到了一万多单委托请求,但实际受理的只有两三千单。
“直觉上这个单子可以‘什么都不做’,我就接,不行就拒绝。类似‘能不能帮我买某件东西’的跑腿请求,我一般都推掉。不过,判断标准还是比较任性,全凭心情。”
最初在推特发出租广告时,森本没有料到会有如此多委托。甚至有那种吓他一跳的:“有个客户想让我听他讲‘杀过一个人的经历’,因为不能告诉别人,他憋得实在难受。还有客户说他以前是某个宗教组织的信徒,但这个组织被社会强烈批判,他想让我听听他的想法。”
他也观察到这两年间邀约的变化:从一些无足轻重的委托——比如陪客户吃饭、排队,到更实用的委托——类似陪着逃班、打扫房间卫生,后来更私密的委托也多了起来,例如“这件事我不能告诉任何人,只想说给你听。”森本也因此充当了东京人秘密与情感的泄洪出口。

于是,无可避免地,森本会撞上客户的“人生重要时刻”。他接到过“请与我一起提交离婚申请”的请求,一位女士想让他见证“脱离夫姓,重新拥有自己的原本姓名和全新生活”的瞬间。
还有一次,他遇上“想知道丈夫出轨短信真伪”的委托人,也就跟着目睹了一场伤心:委托人在看到决定性证据的那一刻,立即将自己的脸埋进手掌里。
疫情期间,涌向森本的委托也越来越多,尤其是“请听我说”的请求。有人发私信给他:“我超喜欢的偶像演了个超无聊的剧,你可不可以给电视台打个视频电话说一下,我旁观?”
还有很多来自医疗工作者和药店店员的委托,“因为抗疫太疲惫了,想让我听他们倒倒苦水”。

图/《什么都不做的出租先生》
因为疫情的缘故,很多委托人心情沉重。
有些人在职业感染风险高、工作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同时还担负着保密义务,因此不能向森本倾诉具体细节,“与其说是分享工作内容,不如说更像希望表达心情的委托”。
另外,例如干洗店的工作,虽然不属于高风险职业,也有不安的从业人员联系他。“实际上,很多人都在充满恐惧地工作,但因为不是停业补偿的对象,所以还在继续营业。”
反之,也有人倾诉“多亏了疫情,人生才变得快乐”。已经停课的一位老师告诉森本:“一直以来都负责学校事务,照顾学生的工作让我不知所措。学校关闭以后,我有了私人时间,现在终于可以享受生活了。”
不能对相熟亲友言说、不能为主流价值观所认可的很多心情,都汇聚到森本这个东京“树洞”里。

记者在社交媒体上私信森本,询问他是否方便接受采访,森本秒回。

尽管森本总能和不同的人相遇,也见证过许多曲折故事,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会做什么有“意义”的事情,他也没有参与甚至干预别人生活的欲望。
在日本媒体的一次采访里,他诚实回答,“现场的气氛和人心都完全看不懂”——说着什么都不做的人,果然只是在委托人身边“无为”地虚度了几个小时。实际上,在推特发布出租广告时,他也想过“移动的摆设”这个名字。

对于每次委托,是仅仅提供“不投入任何感情的单纯陪伴服务”,还是也会贴近别人的心情?
森本说:“其实会带有一些感情,但没有刻意暗示自己要隐藏起来。可能我本身就属于感情不外露的类型,即便对客户感同身受,我猜对方也完全没有察觉到。我只是对他们提出委托的动机感兴趣,没想过要贴近别人的心情。”
他其实更享受能接触到“自己平时想不到的事情”和“超出自己理解范围的事情”。“对于客户来说,贴近心情也容易让对方不舒服吧。拿我自己来说,我就没想过谁能贴近我的心情,反而会很抵触,会觉得‘理解我的心情?可别自以为是了!’。所以,即便‘贴近心情’,肯定不是出于为客户着想,我也不会为此而白费力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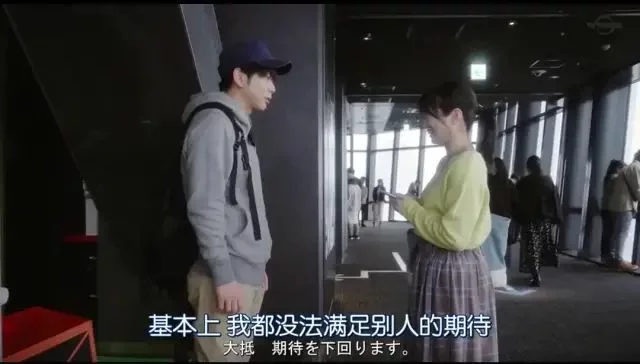
虽然不作干预,也不产生多余的共情,但纷至沓来的委托也揭示了这样的事实:森本的确提供了一种众望所归的价值。
一位看似粗犷的大叔曾委托森本到卡拉OK听自己用假声唱《邻家的龙猫》。这个腼腆的中年人特别喜欢唱歌,但因为有些音痴,总是一个人去没有观众的练歌房。许多年前,他被初中同学取笑的场景仍历历在目,时间长了甚至“连自己都觉得好难听”。
为此,他一个人偷偷练习了很久,觉得“应该不会那么难听了吧”,很想让别人来看看他的练习成果。同时,他深知走上社会后,身边没有人会不礼貌地直言自己不好,因此更希望能得到真实评价。
直到陌生人森本客观地说出“唱得很好”,大叔终于松了一口气:“今天真好,谢谢。”
还有年轻女生邀请他尝尝自己做的饭菜:“以前我喜欢做饭,别人都说好吃,但不知什么时候起我做饭被大家认为是理所应当的事了。”面对来吃饭的朋友,她也总是在意别人的评价,期待得到感谢和称赞,如此一来双方都有社交压力。
她想着,要是出租先生来就不会抱有高期待了,可以单纯地享受做饭与吃饭,“有人来,比来的人给我反馈更重要”。

平时经常请别人吃饭的一个客户想跟森本约饭,只因为“请客太费心,这次我只想好好品尝料理”。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的爱好者也希望跟森本观看比赛,“和自己一样了解棒球的人去看,反而撞意见,所以想和不太了解棒球的人观看”。
每当看到这些平时秘而不宣、难以洞察甚至不值一提的想法时,森本都会感叹,“人还真是有不可思议的需求啊”。
向森本发出委托请求的,是一群需要被证实“自我存在着”的人。他们希望自己的生活有人在场,但也希望拥有“空气一般”安全的社交距离。
森本认为,他提供的“只是作为一个人存在的价值”,如果还要附加什么,也可以说,“只是作为一个‘安全’的人存在”。“通常来讲,和人接触未必那么安全,至少让对方觉得我在身心上都不会伤害别人,这点也算价值的一部分。”

另外一部分价值还在于,他提供了“临时的人际关系”。毕竟人际关系也是压力来源,如果让熟人陪自己办事,以后免不了要还人情。“之后不会和我产生人际关系”这一点,也是森本的出租服务延伸的价值,“为人际关系而苦恼的客户还挺多的”。
选择和陌生人倾诉内心的委托人不乏这种顾虑:如果把烦恼和秘密告诉朋友,关系恶化时,就会被对方抓住把柄;面对一些很大的烦恼,亲朋容易过于担心或过度建议,也会给自己造成压力。
森本曾为职场人际关系感到苦恼,但现在他的“出租工作”规避了固定的人际关系,转向了流动、临时的人际关系,以前的烦恼也随之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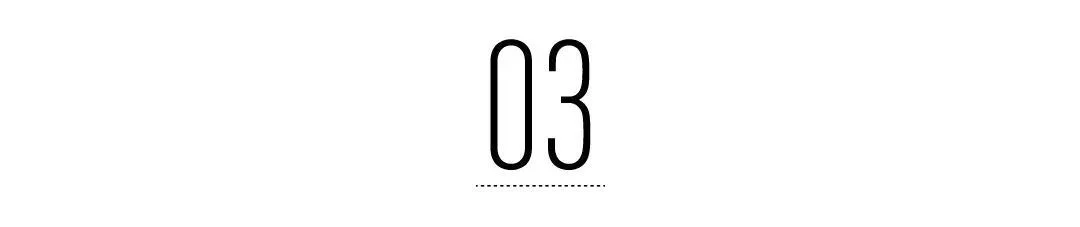
日本亚马逊上,有网友将《什么都不做的出租先生》一书类比为舍伍德·安德森笔下的《小城畸人》。
在这部短篇故事集里,舍伍德·安德森通过青年威拉德的视角聚焦住在乌有之乡的各色居民,触及他们不被关注的内心微妙之处,也折射了他们强烈鲜明的个性。森本也像一条线索,调动了隐匿于社会中已久的“乌有之乡居民”个性的现身。
有些读者认为,森本的身份“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是场所”,委托者不需要他为自己提供切实的劳务,只想“借他的存在”完成生命中的某些时刻。

也有读者对他进行指摘:“不想出生在这样的父亲家里。”“读无力大叔生活日记没有价值。” “不贴近对方的心情,真是彻底贯彻了什么都不做。”
实际上,大部分委托人基本上是“有所事事”,而森本的业务情境通常是:作为世外闲人以“什么都不做”的状态旁观别人“做事”。对此,他倒没产生焦虑感,对于 “逃避现实”的指责,他直言:“有些人就是想对我进行说教,我本质上非常讨厌被说教。”
日本政府因2019年国内出生人数不足90万而焦虑不安,《经济新闻》更指责“有不工作的蚂蚁”。一部分生活在“努力奋斗”主流价值观下的日本读者从森本的经历得到启发:“不动的蚂蚁不是坏人,不工作的人也不是坏人。”
“无所事事的人试图核实一个问题,即人类是否可以不做任何事情就可以生存,或者存在本身是否就已经是有价值的。如果认为自己即使无所作为也照样拥有生命价值,那就是最强的自我肯定了。”

日剧《什么都不做的出租先生》里有一句台词: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什么都不做”比“做些什么”更难,更需要勇气。
这也许是来自编剧的个人感慨,但森本不这么觉得:“这要取决于每个人更适合什么。要是有人觉得什么都不做更难、更需要勇气,去做些什么不就好了?我现在以‘什么都不做’为职业,这就是最适合我的工作,所以我挺快乐的。”
最近,森本每单委托要收费1万日元。最初提供出租服务时,他只收交通费和餐饮费,不收劳务费。虽然不是公益行为,也算不上正经工作,“说是个人兴趣也不太准确。可能我的初心有社会实践的成分,也有积累采访资料的念头。但说实话,多少有点想突破循规蹈矩的想法,就是不想被归为某一类。后来也是不知不觉发展到收费这一步的,也算是实践的一部分吧”。
即使很长一段时期没有稳定收入,森本的家人依然支持他的选择。
“我太太觉得这件事蛮有趣的,尤其是出了书、拍了电视剧,她会说:‘好棒啊!’我儿子当时只有一岁,什么都不懂,现在三岁了,看到电视剧后,儿子会跟我说:‘什么都不做的出租先生来啦!’还让我学剧中主人公戴帽子,我一戴上,他就开心地笑起来。”
采访过程中,森本对很多问题的回答都不甚明确,也不热衷发表主观评价,他说,除了自己的感官和经验,其他的都是“我不知道”。但有一件事,他回答得迅速且笃定:“我是一个不在意社会价值标准的人。”
被问及“对什么都不做这件事的热爱会持续到什么时候?不会因为无所作为而感到厌倦或痛苦吗?”时,森本说:“以后的事情谁知道呢,一切皆有可能,不如不想。我也没感到痛苦,只能说有一些不愉快,但这种多元化和转瞬即逝的东西,也是快乐的一部分。”

《小城畸人》的类比相当精妙。无聊乏味的小城中,日复一日的生活乍看平凡无奇,然而畸人隐身其中。
舍伍德·安德森在书中写到,起初,这个世界还很年轻的时候,有许许多多思想,却没有真理这种东西。真理是人自己创造的,每个真理都是众多模糊思想的混合物。真理成千上万,而且都很美丽。然后,人出现了。每个人出现时都抓着一个真理,有些特别强壮的甚至抓着一打。真理让人变成畸人。
一个人一旦将一条真理据为己有,称它为自己的真理,并且尽力按照它去生活,他就成了畸人,他拥抱的真理也就成为谬论。
森本坚持的也许是别人眼中的“谬论”,却是他自己认定的“真理”。
于是,在万人如海的东京,森本祥司出现了。
(编辑:月儿)
315记者摄影家网,“出租先生”,森本祥司,最擅长,什么也不做







 体重轻就能半价旅游?提防“低价游”新套路
体重轻就能半价旅游?提防“低价游”新套路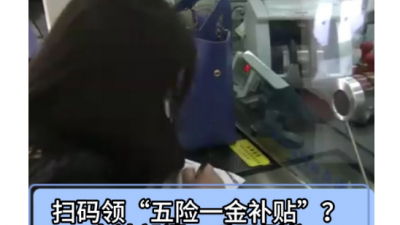 扫码领“五险一金补贴”?当心,是诈骗!
扫码领“五险一金补贴”?当心,是诈骗! 探秘 “银发专属健身房”:解锁老年健康社交新密码
探秘 “银发专属健身房”:解锁老年健康社交新密码 网络交友小心“甜蜜陷阱”
网络交友小心“甜蜜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