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五届单向街书店文学节“十年之后”主题演讲中,作家、前媒体人袁凌真诚地分享了他的十年人生,失败、挫折、打击都被他以诙谐的言语轻松化解。
十年,不惑之惑
撰文:袁凌
我这个人其实不像是世界的水手,水手们可能是主动去拥抱欢迎时代,对社会的变化很敏感,也很欢迎。我是一个后知后觉的人,很别扭地被时代强行推着,进一步退两步这样被推着走过了十年。所以在这样一种过程中,难免会有很多的困惑。
这个十年恰恰又是我个人的年龄从三十几岁接近不惑之年,到现在已经接近知天命之年的十年。当初在十年之前,我接近不惑十年的时候,我是非常困惑的,到现在我也一点不知道自己将来命运到底会怎样。

▲“十年之后”演讲现场

▲袁凌在“十年之后”主题演讲中
虽然如此,我毕竟还在生活着,所以我也努力地在这种不确定性之中寻找一点内心的确定性。这个确定性是什么?我想也只能找到我们自己正在做的一些事情。而我眼下还在做的,能够做的,也就是码字。至于这个字码出来是什么样子,能码多好,我现在也真的还不知道。
我想把十年分三个方面跟大家交流一下,其实很多人大体都有这样一个模式,但是我可能有一些个人的特征。
这三个方面,一个就是我作为一个曾经的传统媒体人,到后来变成一个新媒体人,到后来出局了的过程,一个行业身份变化。第二个是我个人写作的创作形态变化。第三个是我个人跟国家、故乡、城市有关的生活经历变化。这三个方面构成了我的十年。
先从第一个方面说起,职业身份的变化。在十年之前,也就是 2009 年的时候,我是一个传统媒体的传统媒体人,做着很传统的新闻形态,就是调查报道。我根本没有想到后面会出现特稿这种东西,甚至会出现非虚构写作。
我当时以为也就是这么做下去了。从职业上,根本没有想到会有后来的变化。但是后来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变化了。首先是我离开了比较有官方背景的传媒,到了一个号称是“集纳海外两岸三地华人视角”的这么一个杂志,《凤凰周刊》。后来又因为一个很特别的原因,就是我自己在不合时宜的时机,在不合时宜的地方,出了一本不合时宜的书,然后深夜就被杂志社的主编约谈,掏出三份文件让我签字,立刻离开,发生的所有事情跟杂志社没有任何关系。

▲袁凌,1973 年生于陕西平利,出版《寂静的孩子》、《青苔不会消失》《世界》《我的九十九次死亡》《在唐诗中穿行》《从出生地开始》、《我们的命是这么土》等书,新京报·腾讯 2017 年度致敬青年作家,腾讯 2015 年度非虚构作家,曾获新浪十大好书、华文十大好书、南方都市报十大好书等奖项。
我当时也很不想麻烦人家,我就签了,签完之后从此就离开了传统媒体。从 99 年开始,我到传统媒体,2016 年离开,我真的是没有想到这个事是这么结束的。中间我曾经好几次离开,又好几次回去,还是试图想在纸媒一直待着,写有深度的报道,即使后来开始写特稿,也是一样的想法,人家也曾经许诺跟我说可以养老,但没想到就这样突然就结束了。
然后我就到了新媒体,刚开始日子也有点舒服,也不用干太多活,给你一个保底,算是互相利用吧。初创的草台班子,跟我这种非知名作家互相利用。但等到后来人家越做越大,引入了一些资本方之后,再加上又遭遇资本寒流,资本方表示不养闲人了。就解约吧。我也不好意思说什么,毕竟人家都养我两年了。其实在这两年之中,我都经常感到惶惶不安。我在想这种好日子会有多久,什么时候会结束?所以当它有一天来到的时候,我也觉得没什么好说的,那就结束吧,然后我就变成了一个没有单位的人。这也意味着我从此真的离开了媒体。
回想起来我从 99 年开始在日报,到后来到《新京报》,到《凤凰周刊》,从做热线新闻到国际新闻、商业新闻,到后来做经济新闻,做深度报道、调查报道,后来写特稿,然后是非虚构写作 ,期间一直是在媒体待着,终于走到了一个结束,不仅离开了传统媒体,也离开了新媒体。
我的好多同事,当然他们早就离开了,但他们离开是主动的,外面有黄金万两,不一定要潜入春江。有的人走的时候还要写下一封公开信,说传统媒体没戏,你们这些还不走的人真是傻,又傻又无能。但那个时候我也没想走,我傻就傻了,无能就无能,我就待着。但没想到后来真的还是只能走。
走了以后,我发现外面一两银子也没有。怎么办,只有靠自己码点字了。我也不想学那些人,走的时候还要把别人鄙视一下。但这个时代确实是让传统媒体衰落了,新媒体是不错,但说实话,它真的是在水里面拼命地游,那水可不是春江。可能是秋江、冬江。我有一个兄弟,也是莫名其妙被从他们那个地儿开掉,还进去待了一段时间。出来之后现在做个人公众号。我看他做的,就是刀口舔血这样的营生,搞一点流量,挣一点钱,真的也不容易。

▲袁凌在“十年之后”主题演讲中
接下里说到我个人的写作。十年之前,我那时候理想是扎根农村,写农村的小说,做一个陶渊明。一心想的是这样,即使我 2006 年第一次回到农村就已经失败了,但到 2009 年,我还想再尝试一次,回去待了四个月,然后彻底完蛋,又出来了。当时就一片茫然,没办法,就继续写,写得都是一些不知道什么样的东西,那些东西完全发表不了。
你一拿过去,人家文学杂志说,写得不错还挺感人的,语言不错,但是不像小说,搞得我就一点办法都没有。我记得我有十年时间没有发表过一篇东西,那时候也不像现在这样到处是公众号,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只能一边工作一边写,好歹还有媒体的饭碗。就这么写,不知道哪一天,调查报道写得好好的,突然可以写特稿了,我本来挺不情愿写特稿的,但后来实在写不动调查报道了,那行吧,写一篇试试。
写着写着感觉还可以啊,又省力,比调查报道容易得多,还容易出名。接着非虚构这个概念跑出来了,这东西怎么就这么适合装我的东西,我的土豆装到这个筐里特合适。原来那个筐,我是一点机会都没有。然而现在就这样莫名其妙上了非虚构这条船。
到了 2014 年的时候,我开始出书,第一本书是《我的九十九次死亡》,以前这本书的书稿至少被十家杂志社拒绝过。还好在非虚构的背景下,理想国接纳了它。我以前是自费出过诗集的。出了 2000 本,就卖了几百本,其他全码在家里了。后来实在受不了,我说你们谁出快递费,一次给你们一箱,顺丰快递,到付,都给寄出去了,我现在只留了四五本。
《我的九十九次死亡》是我的第一本非自费出版作品,算上它,到现在已经出版了四五本非虚构方面的书,大家比较熟悉的有那么两三本,还有一些小的大家不知道。另外还有我在不合时宜的地方出了的那本不合时宜的非虚构,一分钱都没捞到,还丢掉了工作。但最近我听到一个不错的消息,有个朋友到美国去拜访李泽厚、刘再复。他们不知道是怎么看到了这本书,还夸奖了这本书。咱钱得不到,但至少得到了一点安慰。

《我的九十九次死亡》
袁凌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
这就是这几年我写非虚构的经历。同时我当然也写其他类型的,比如小说,我也出过两本小说集,但是小说确实不如非虚构卖得好,因为人家把你看成一个带着非虚构标签的作者。
写到现在,有时候也挺困惑。我并不想把自己局限为一个非虚构作者,但是别人就觉得,拿这个概念好使,别的不好使。但是非虚构这个概念,实际上并没有被真正地接受。虽然现在大家经常说,好像也挺熟悉的。但实际上有几部真正有分量的作品?有几个是大家承认的作家?我记得前段时间,有人采访我,把我叫做一个“非虚构记者”,我觉得这个挺意思,记者本来就是真的,难道有虚构的记者吗?
但我猜可能他是觉得叫我非虚构作家有点奇怪,大家也不熟悉。叫作家也不太像,那叫记者,好像又不是传统的记者,所以叫非虚构记者。还有一个媒体报道说我是“知名爆料人”,我心想,天哪,我什么时候要当爆料人了。所以这种写作形态蛮尴尬的,但现在也只好这么先写下去。
接下来就要说我的人生,我的人生在这十年当中,其实变化也蛮大的。十年之前,像我刚才说的,当时待在农村,想扎根乡土不出来了,后来被迫回到了上海,在上海到待了一年之后,觉得特别孤独,一点机会都没有,任何方面都没有机会。
然后我就到了北京,后来又来回折腾了几次。但是近几年北京变得好像越来越没什么意思了,好多人都走了,气氛也不见了,我就想着怎么办呢?人也老了。在这儿也没有什么稳定的社保,也没有户口,也没有房子。我想是不是该找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家乡也待不住了,找一个二线城市吧?找个省城?是不是回到我们陕西省省城去?现在已经把户口转过去了,但是这样的话,北京的那些东西是不是得丢了呢?比如像是今天这样的机会。
我觉得这几年,这个时代给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就是我们到底待在哪里。这里面既有身份的困惑,也有现实的疑难,我也不是一个体制内的作家。虽然说我写作,现在可以出书,可以挣点钱,并且也是当前唯一的经济来源。但是未来天花板谁知道会降到什么程度,明年还能不能出书,还过不过得了审?写的东西有没人要看?有没有那么讨喜?我想这些都是我自己没有办法去预测的事情。
我到底将来会在哪里?我到底算是哪里人?回归农村的希望失败了,那现在我算不算城里人?我觉得我永远是一个漂的角色,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不管在写作形态上,在这行业身份上,在个人的生涯上,都有些困惑。但是我想我还是有不困惑的地方,就是我现在能做的,先写点字吧。也许选择多了就不知道要做什么,既然现在只有这么一个选择,那就先写吧。到哪天如果不让发了,如果没人要看了,实在不行了,我们还可以学瓦茨拉夫·哈维尔嘛,学那些捷克的作家,我可以干体力活,干不动了再说。有一口饭吃的时候,我就先写。现在只能这么想了,这也就是我在“惑”当中的一个“不惑”吧。
去年从新媒体被人家解约的时候,我写了一首诗,古体的打油诗。它能够大体代表我现在的心境和想法,我给大家念一下。
又到岁暮叙飘零,三度失业愧世情。
两肘清风华盖运,一生辗转驿马星。
斯人自古唯寂寞,儒冠从来多误身。
虚名实惠复何计,穷文败笔安此心。
能得到的实惠已经很少了,虚名这个东西也太虚了,文字到底写得好不好,也不知道。但是在这些很失败、很局促、很苍白、很卑微的文字里,在这种并不伟大而恰恰是很小的东西里面,我可以找到我安身立命的所在。我想有时候,理想是不管用的,荣誉也靠不住,但在自己最低的位置,最低那个点,我想是可以安心的。现在我正在这个比较低而且还能够做一件事的位置上,那我就继续这么做下去吧。
*本文由袁凌在第五届书店文学节暨单读十周年“十年之后”主题演讲整理而成。
(编辑:红研)
《科学导报今日文教》征稿可发新闻、政工论坛、学术论文、课题研究、讲座、学生作文、书画、摄影作品、传记、专家、企业专访、广告软文等,欢迎投稿。国内统一刊号:CN37—0016,邮发代号:23—139 电话:010-89456159 微信:15011204522 QQ:1062421792







 体重轻就能半价旅游?提防“低价游”新套路
体重轻就能半价旅游?提防“低价游”新套路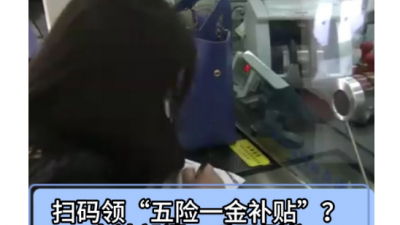 扫码领“五险一金补贴”?当心,是诈骗!
扫码领“五险一金补贴”?当心,是诈骗! 探秘 “银发专属健身房”:解锁老年健康社交新密码
探秘 “银发专属健身房”:解锁老年健康社交新密码 网络交友小心“甜蜜陷阱”
网络交友小心“甜蜜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