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的树大都是普通、质朴的,它们穿着家织布衣衫,粗手大脚地站在那儿,叫你一看就觉得特别的亲切。其实它们多数也开花,这还不是指桃、杏、梨、苹果之类结果子的树,而是说那些不结果子、长成后只作木材用的乔木。当然,它们的花少有南方丹桂、白榕、广玉兰花的清雅,也非凤凰树、火焰木、蓝花楹那么娇艳,极为朴素,朴素得不被人当花看。早春,杨树的花像一只只缩着小脑袋的毛毛虫(不免显得有点儿丑陋),柳树的花也没有透明漂亮的花蕾,这都是为了躲避倒春寒的袭击、伤害。我在鲁北一带见到一种能开好看的花的树,它叫梧桐,梧桐花开在四月初,淡紫色,瓣儿很大,成串成簇,还吐着浓郁的香气。或许只在几家的庭院、房前屋后有梧桐树,但却好像整个村庄都笼罩在团团彤云和芬芳里。有时候,村头别的树丛中冒出了一两篷开花的梧桐树冠,我的眼睛登时就点亮了,心被那热热的气息撩拨得不行,我真想上前喊一声“大嫂”——是的,她们是我热情而温厚的乡村大嫂!
有这般印象的,还不能不说到槐树。它的花是白色的,也一嘟噜一嘟噜的满树都是,纯朴、大方、豪爽。槐树较之梧桐,感情上与我们更近一层,那花儿苦中带甜,能食用,饥荒年月可帮穷人填饱肚皮;富足的日子,吃腻了大鱼大肉,又怀念它的清淡。我吃槐花长大,从小喜欢爬门口的歪脖子槐树玩耍,但若说仔细观赏它,欣赏它的美,却从未有过;在鲁北,它比梧桐普遍一些,到处可见,便不能再吸引我多瞥一眼。不过,我们这次要去的是孤岛槐林,据说它有七万亩之大,七万亩槐树一起开花,那是什么景观?无边的汹涌海浪?不尽的连绵雪岭?嗬,我要大饱眼福了!
可惜,我们来晚了。今年春天无雪无雨,天气出奇的暖和,槐花开得早,等我们来到孤岛,盛花期已过。我们只能在槐林里趟一趟没了脚背的落英,一旁瞧着放蜂人从帐篷里一桶一桶地往外搬槐花蜜出售……
但是,置身于繁花抖尽、新叶拱出、枝桠遮天蔽日的槐林,望着它森森然、莽莽然、浩荡甩开,与天边的一抹黛绿相接、相融,我起初的失望在被渐渐升腾的振奋感替代:观花固然好,通常都是观花,今日我们不妨看树!
美丽的孤岛原先是被称作“大荒原”的,为退海之地,不生草,不长树,唯有白茫茫的碱花和充塞天地间的死寂。上世纪50年代以后,军马场人、胜利石油人、还有鲁西南梁山阳谷等县扶老携幼逃荒的灾民,以踏踏的马蹄、隆隆的钻机、吱扭吱扭的独轮车和“大开发”的号子闹醒了它,随即沙子路、柏油路、高压线及传书鸿雁的轨迹扯进荒原深处。那时这里有一句顺口溜在内地不胫而走:“孤岛兔子大如牛,电线杆子比树多”。乍听以为是骚文人编瞎话,后来有机会来了一趟孤岛,才知道下半句并不离谱。至今孤岛的鸟儿们还有在电线杆子上筑巢的习惯(传统没有丢),恐怕在五大洲这也算得上是身怀绝技。“一棵树”的故事更叫人过耳不忘,说的是方圆几十里只有一棵柳树(不知哪只可敬的鸟衔来的种子),在附近劳作的人若能抢在这棵树下歇一歇,那可真是好运气。渺无人烟的荒原上难以辨别方向,谁要是迷了路就找这棵树。如同大海里的一座灯塔,这棵树无声地凝聚着人心。慢慢地,“一棵树”成了一个地名,成了一个村镇。后来这棵树死了,人们为它立了碑——为一棵不是贵族血统的柳树立碑古今稀罕!这片荒滩,因为沉积了太多的黄河水裹挟来的泥沙,不分春夏秋冬,狂风与黄沙勾结,肆虐逞凶,横冲直撞,搅得天昏地暗。拓荒人恨得牙根发痒:把这条黄龙缚住!于是,他们精选苗木,用心血汗水浇灌,誓让这不长树的地方长树。一年,十年,二十年……便有了这七万亩槐林,有了这撒遍荒原的太清树、榆树、白腊、柳树、杨树、梧桐的混交林,有了这一道道坚不可摧的绿色屏障!
我一个人默默地在林子里,走走,停停。我是在寻找什么吗?我注意到这些树的皮肤都这么粗糙,远不像空气湿润的南方,树干光洁柔滑,这显然是风沙常年吹打、刻蚀所致。但它们的肌块却格外结实,有着北方汉子瘦硬的肢体。我忍不住抚摸它们,啊,一杆杆都是温热的,无疑,青春的血液正从根部往梢头涌流。这是一些鲜活而强健的生命!我又发现了一个“秘密”,这些树几乎没有一棵上下直溜溜,都倾斜着身子;没有一棵是依傍青山绿水而生的树那优雅的模样,一律困境中搏斗、抗争的姿势。弓着背的,猫着腰的,舞着长戟的,挥着短剑的……我能想象出“反击战”是多么惨烈,树们英勇无畏,斗志昂扬,怒吼着挺身而出;风沙恼羞成怒,百倍疯狂,恶狠狠扑过来。短兵相接,撕扯扭打,你死我活,难分难解。一场战斗结束,多少树折断筋骨,皮开肉绽,它们趔趔趄趄,东倒西歪,没丁点儿力气了,而“顽敌”又发起新一轮的进攻……一天天,一天天,岁月凝定了这一切,完成了这悲壮的雕塑!……此刻,处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我却分明嗅到这背后经久不散的刺鼻的血腥味!
可能是在捕捉灵感的文友小林,从那边“转”到了我这里。眉清目秀、细高挑个儿的她,扛着一根“炮筒子”对准我,要给我拍照。我特意选了一棵眼看就扑跌在地、并且肢残的老树作背景,不,是我和它合影,我要与它并肩而立。小林面露诧异之色,她来自风光旖旎的海滨城市,不了解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但我没向她解释,这得用心体悟。在我眼里,这棵与风沙苦斗了几十年、一点点变矮的树仍然十分高大,是我应该仰视的英雄。
脉管在鼓胀,胸口起伏,我萌生了一个心愿:看一看孤岛所有英雄的树,成排成阵的看,分散零落的也看!但靠步行是办不到的,不得已只好乘车。在车上,我趴在窗口,两眼一眨不眨。可树从窗外掠过,瞬间即逝。灵机一动,打开相机,我要把它们动人的英姿拍下来!我接连不断地揿快门,身边的小林直笑我不会取景。不错,这些不妩媚、不风情、只有铜干铁枝的树好像没有资格进入镜头,但难道它们不是大地上最美的景致?只遗憾我的相机不带长焦,无法把远处的树拉到跟前,远处那些或独处或三两株相依相偎的树已经模糊了面目,没有人向那里张望,甚至连它们的名字都不为人知。这是我的不平,它们活着并不是为了这,它们默默地呆在那寂寞、冷清、被遗忘的角落,只是想为守护后方的现代化城市尽一份力。
请勿忽略了这幅风景画上最浓重的一笔——在行行树的队列里,有为数不少的死树——死了,它们也不倒下——可看上去这些死树并不弱小,反而多是树身粗壮、枝柯纷繁的“伟丈夫”,可以想见活着的时候它们是怎样哗啦啦高举着绿色的大旗!“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但风沙的“明枪”没能使它们败下阵呀,遭了啥“暗器”不成?原来,罪恶的盐碱不曾走远,就藏在不足一米的地下,一般树种根一触到盐碱层,再茂盛也将萎叶、焦梢、枯干。所以这里的树都长不很大,寿命不长,生命在华彩乐段就突然中止。这是它们不能改变的宿命。但是,在这没有古树、没有树神的地方却不乏后来者,一棵死去,十棵新生;你高出我的头,我蹿过你的膀子;一茬一茬,一代一代。后来者明明清楚前辈的厄运,却依然满怀信心、一步不落地跟上;前仆后继,薪尽火传,它们要像传递接力棒一样把希望的火种传递下去!你看路边、河滩、土坎上、野地里那一群群小树,也就是十来岁的孩子吧,前头还有更小的,六七岁、四五岁……它们沐浴着金色的阳光,通体透亮,是那么活泼可爱。路拐弯处,忽地窜出一帮虎头虎脑的“野小子”,摇着墨绿的小手掌,欢笑着,蹦蹦跳跳地迎着我们的车跑过来了、跑过来了……注视着它们的身影,流连在这块热土上,我懂了:谁也不能阻挡生命的脚步;它们永远年轻;倘若有可以永恒的生命,它们便是……
作者简介:李登建,邹平明集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山东省作协散文创作委员会副主任,山东省散文学会副会长兼创作委员会主任,滨州市作协主席,一级作家,山东省作家协会首批签约作家。散文作品300余篇次被《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百年中国散文经典》《新中国60年文学大系·散文精选》《世界美文观止》等书刊转载和收录,《千年乡路》等十余篇散文入选部分省市高中语文必修教材、高考语文摹拟试卷和中学生读书竞赛阅读篇目、现代文阅读训练习题,曾获得首届齐鲁文学奖、第二届泰山文艺奖,山东省第六届、第九届、第十一届“精品工程”奖,首届“奎虚图书奖”,中国当代散文奖,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作品等奖项。
(编辑:李月)







 体重轻就能半价旅游?提防“低价游”新套路
体重轻就能半价旅游?提防“低价游”新套路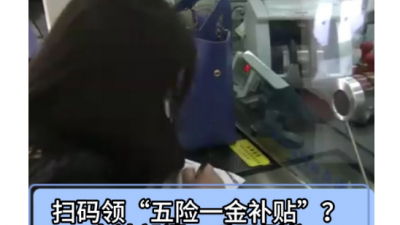 扫码领“五险一金补贴”?当心,是诈骗!
扫码领“五险一金补贴”?当心,是诈骗! 探秘 “银发专属健身房”:解锁老年健康社交新密码
探秘 “银发专属健身房”:解锁老年健康社交新密码 网络交友小心“甜蜜陷阱”
网络交友小心“甜蜜陷阱”